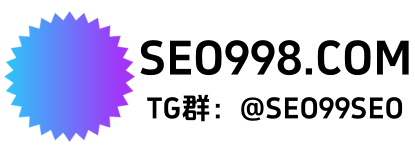飞华健康网:朝阳群众吃瓜网黑料-吃瓜 黑料不打烊-“非思”的思想——探索失语者的思想史
从清末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对“民史”的提倡,到世纪之交围绕斯皮瓦克提出的“底层人能说话吗?”这一问题的讨论,再到时下“新革命史”倡导者所致力的发掘“普通民众的主体性”工作,这既彰显出中国学界对底层民众的持续性关注,同时亦暗含历史书写范式从过去聚焦国家建构以及精英人物活动实践等宏大叙事向普通民众的日常微观世界的转变。然而,无论是学界的关注,抑或是历史书写范式的转变,这仅仅是将底层民众作为历史整体构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加以彰显,但却并不意味着他们主体性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而言,底层民众的所言与所思,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大卫·格雷伯曾在《人类新史》中讲道:“思想史家从未真正放弃‘伟人’史观。在他们的记述下,好像一个特定时代所有重要的思想都可以追溯到某一个或一些了不起的个体身上——无论是柏拉图、孔子、亚当·斯密还是卡尔·马克思。”确然,正是受制于特定的权势话语或者精英话语,底层民众长期以来被视为失语者。即便有所发声与行动,但这些言行举止却未曾纳入到思想范畴并加以认真对待。实际上,底层民众已然拥有思考与想象的能力,只不过他们的呈现方式与伟人或者精英有所殊异,用朗西埃的话来形容,底层民众的思想属于另类的思想,即“非思”的思想,这种“非思”的思想并不像精英话语那般具有逻辑性和系统性,故而时常被排除在可见的范围。正因如此,底层民众的思想从被遮蔽的状态到自主呈现的过程,其实可以视为从宏大叙事或者精英话语之中突围的过程,或者说从既定的垄断性与统制性叙事中解放出来的过程,这一过程并不是通过简单的话语置换所能实现,而是需要从他们独特的言说方式出发,掘采属于其自身的思想特质与潜能,进而将这种潜能转化为抵抗的动能。无疑,朗西埃“非思”的思想所要传达的内容,既涉及潜能的展示,又关乎主体的确立,更甚指向解放的实现,若以此概念工具为线索展开对底层民众的思想及其动能的探索,这就颇显必要与重要。

法国左翼理论家朗西埃
作为法国左翼理论家朗西埃,其在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一直对底层劳工生活现状及其斗争实践保持长期的关注,而“非思”的思想的提出,正与这一关注有着紧密的关联。朗西埃在《默然言说的两种形式》一文中讲道,思想的呈现方式或者形态是多样的,但有一种较为特殊,那就是“非思”的思想。何谓“非思”的思想,朗西埃继续补充道,“存在一种非思的思想,思想不仅是不同于非思的元素,也是以非思形式来运行的。存在着内在于思想之中的非思,思想赋予非思一种特殊的力量”;不唯如此,“非思”是思想的“对立面的实际出场。从任何一个方向出发,我们都能触及这个等式,即思想与非思的统一”。(朗西埃:《审美无意识》,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9—27页。)据此分析,朗西埃一则将“非思”作为思想的特殊形态进行肯认,另则又区分了“非思”与思想二者间的异同。当然,这番解释,实际上折射出“非思”的三项重要特质,一是“非思”并不像思想那样出现在显见的位置,其往往被特定的缘由所遮蔽或者忽视,而藏身在思想的后台,尽管如此,“非思”同样内具着思想的力量;二是“非思”的这种力量虽然内在于思想之中,但其可能挣脱思想的牢笼,并且以思想的“对立面”形式出场,最终对思想本身进行解构;三是“非思”对于思想的解构,并不是消解思想本身,而是在以一种超越性的维度对思想进行重塑。
“非思”既然是思想的另类形式,这就意味着它并不是“不说”或者“沉默”,而是以独特的方式在言说,但这些言说方式往往被特定阶层的垄断性思想话语所遮蔽,因此在有形无形之中形成对“非思”的忽视。从传统的观点来看,“思想”一词,往往被视作统治阶层、历史伟人或者知识精英的创造物,而与之相对的底层民众,一则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沉默的,甚至说成是无声的,二则认为他们即便存在自己的想法,也不能提升到思想的维度与高度,结果只能由知识精英来代言。鉴此,朗西埃借用十八世纪德国浪漫派诗人和矿物学家诺瓦利斯所述的“万物在言说”一语,开始展开对这套深固的思想话语的批判。朗西埃指出,“万物就是痕迹、遗迹或化石。所有感性形式,从石头或贝壳开始,为我们讲故事。在它们的纹路和褶皱中,它们都承载着历史的痕迹和命运的标记”。所谓“万物在言说”,这其实是关于平等话语的隐喻性表达,“它抛弃了等级制的再现秩序”,同时又彰显了“万物”所“带有语言的力量”。万物在言说,底层民众亦不例外,他们虽然不能像知识精英那样运用系统性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所思与所想,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此失去了表达的“语言”,如若细心地观察,他们正是借助自己的语言和修辞加以抒发,并且通过自己发明的或者创生的概念进行交流,只不过对精英阶层来说这套语言系统是陌生的。在此,“非思”的思想正是指向这一“陌生”的场域,它是由底层民众的语言系统构筑起来的日常世界。不难看出,“非思”之域并不是作为思想的附属物而存在,它正是以思想的“对立面”出场,让以往被视为陌生的场域可视化,进而另外构筑了一个主体场域。
朗西埃对于“非思”的思想的论述,其实需要结合“可感的配置”这一概念进行理解。在朗西埃看来,可感的配置即意味着“在可见者与不可见者之间以及可以被理解者与不能被理解者之间的划分”,换言之,就是打破“可见与不可见、听见与不闻、可想与不可想、可说与不可说”之间的界限,并且重新加以组合与配置。(纪蔚然:《别预期爆炸:洪席耶论美学》,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社有限公司,2017年,第22页。)故此,“非思”的思想,它实际内具着祛蔽性与解放性这两大特质,祛蔽性指向的是不再认定思想只是特定阶级的产物,不再将特定阶级的思想化约为思想存在的唯一状态,或者说不再将特定阶级主导的思想旋律视为思想的唯一旋律;而解放性则是在祛蔽性的基础上,突破既定的思想话语的束缚,以此宣告底层民众的主体性诉求。当然,无论是祛蔽性还是解放性,二者最终的目的指向,则是对思想呈现出的单一性旋律或规范性叙事进行抵抗。底层民众通过运用其语言系统,并以无名的力量在看似难以言明的方式下凝聚,以期在伟人或者知识精英掌控的思想境地,划出一道裂缝,进而寻找一个解放的出口。
问题在于,如何进入到底层民众的日常世界,也就是这片“非思”之域,并发现其解放的潜力,这就需要依赖适恰的方法与正确的线索。所谓方法,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在其自传中曾指出,“了解历史并不意味着记住那些顺序排列的历史事件,它要求你钻进事件相关者的脑子,用他们的眼睛去察看他们的处境”。对于“非思”之域的勘察,正是需要用底层民众的眼睛“去察看他们的处境”,进而“重新思想”底层民众的“那一思想”,如此才能与他们的日常世界和思维习惯相融。在方法之外,同样离不开线索。朗西埃指出“万物”都有自己的“纹路”和“褶皱”,它们“承载着历史的痕迹和命运的标记”,“每一个细节都向我们道出真相”;同理,阿甘本在《万物的签名》一书中亦表示,“万物承担着一个记号”,“凭借记号,人可在各个事物里认出那已被标记的东西”。对于万物来说,“纹路”和“褶皱”既是对它的“标记”,同时也是对它的呈现。“纹路”和“褶皱”虽然不像躯干与枝叶那样显见,但它亦非不可见,只是由于眼光的限制而绕开了这一可见的范域。“非思”之域,其实是可见之域,而进入这片可见之域的线索,就需要聚定目光紧扣属于底层民众的“纹路”和“褶皱”。
对于“纹路”和“褶皱”的寻觅,诗歌是一个突破口。在启蒙话语体系之中,思想往往被视为理性的产物,而由理性所构筑的思想话语,自然拥有着缜密的分析与条贯的逻辑,而“非思”并不遵循既定或者给定的逻辑框架,它可能是断裂的,甚至是错位的。譬如,在1930年代初期,中国左翼文人在上海创办《新诗歌》杂志,这份杂志的《发刊词》就直言,“我们要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纪的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基于如是办刊宗旨,孙石灵发表了《码头工人歌》,该篇诗歌分为四段,每段的开头都是描述工人受到的剥削与压迫的事实,如“从朝搬到夜,从夜搬到朝”,“成天流汗,成天流血”等;而每段段末皆以“大众歌调”即“搬哪!搬哪!唉咿哟呵!”收尾,以此彰工人团结与反抗的心声。然而,诗歌以这样的方式结尾,呈现出两方面意涵,一是对段首设定的逻辑叙述的突围和变异,二是重点凸显这类话语,使其从思想的暗地提升到可见的前台。除此之外,农人劳作的呼声即“啊啊呵,啊啊嘿”,同样也成为这份杂志中常见的诗歌语汇。诸如“唉咿哟呵!”、“啊啊嘿”这类劳动的呼声,看似带有随意性质,但却是由身所感,由心所发,正因如此,通过对这类呼声的发掘,才能够真正进入到底层民众生活世界,也就是说,这类呼声成为理解“非思”之域的“纹路”。相较于统治者或者精英阶级使用的常规性思想表述,底层民众的语言形态,无疑是一种异识,它既缺乏严肃性,又显现出不合时宜性,但正是这种历史的歧出,最终对常规的思想语言形成内在的挑战与超越。用朗西埃的话说,底层民众“实现了一系列将自己身体的生命和语词,以及语词的使用连接起来的言说行动”。

《失业的人》雕塑
“非思”已然不是沉默无声,而是有声抵抗。作为“非思”之域的底层民众世界,他们拥有自己的语言系统,而“纹路”成为进入这套语言系统的关键索引。当然,“非思”呈现出的抵抗性,与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支配与抵抗的艺术》中提出的“潜隐剧本”则不尽相同。斯科特认为,在弱者和强者之间,在从属者与支配者之间,在臣属者与统治者之间,前者出于对后者的害怕、畏怯或恐惧,经常采取某种“表演”,譬如对后者进行拍马屁、恭维、称赞以及歌颂等,这种“公开表演经常被形塑为有权者之期望的迎合”,而这种迎合则被称为“公开剧本”。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开剧本仅仅是弱者“表面上的恭敬”或者出于自保的权宜“策略”,实际上他们在公开剧本之外还存在着一套“潜隐剧本”。所谓“潜隐剧本”,就是“表示发生在‘后台’的话语,而‘后台’是有权者难以直接观察到的”,换言之,潜隐剧本是指“在后台发生的言语、姿势和行为”,它们可能会“否定或扭曲公开剧本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弱者由于意识到公开且直接对抗强者,自然会身陷危境,故而对于强者的抵抗,往往以潜隐剧本的方式展开,比如装傻卖呆、假装糊涂、行动拖沓,甚至是运用闲言碎语、谣言传闻、匿名威胁和巫术等进行反抗实践。这些方式也被称为“弱者的武器”。然而,“非思”的反抗与斯科特论述的潜隐剧本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同样也有着彼此殊异的地方:在相似性层面,二者都重视揭示底层话语或者弱者话语与权势者话语之间的张力,并凸显话语本身的抵抗力量,而相异性则是“非思”的抵抗,消解了公开与潜隐,前台与后台的二元性区隔,相信话语本身就是抵抗的全部,换言之,它并不假定话语形态背后还藏匿着更为深层次的抵抗本质。
福柯在谈论解释技术问题时指出:“如果说解释者必须像挖掘者那样亲身达到深处,那么解释的运动则相反,它是一种凸显、一种逐渐上升的凸显运动,它总是让深度在它的上面以一种越来越可见的方式展开;深度现在被重建为完全表面的秘密。”(汪民安、陈永国编:《尼采的幽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01页。)在福柯看来,解释并不是对“深处”的抵达或者对“深度”的追求,因为事物的本质往往以一种“可见的方式展开”,也就是说,真相或者秘密就在事物的“表面”。同理,对于“非思”的理解,并不需要以“底层的出色挖掘者”现身,作为进入“非思”的索引即“纹路”和“褶皱”,本身就是一种表面的存在,但因为既有的思想话语对此表示否认,并认定表面与真相之间存在或近或远的距离,真相需要穿透表面,直抵其内部深层,才能被揭示。与此相对,“非思”并未遵循这类思想所塑造的现实逻辑,其认定“纹路”和“褶皱”就是真理本身。朗西埃即言:“我们正是要发现这里无所隐藏、字词之内没有什么字词。”这就是说,作为底层民众,尽管他们的语言表达显得支离破碎,或者毫无逻辑,但它们恰恰反映出他们的真实存在。故而,知识精英运用逻辑通贯的线索将支离破碎的语言进行串联,并以此自认这才是底层民众的真实诉求,但实际上,这种逻辑整合可能远偏离甚至背离底层民众的历史世界。张爱玲在《烬余录》中曾讲过这样一段话:“现实这样的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淹没了那点了解。画家、文人、作曲家将零星的、凑巧发现的和谐联系起来,造成艺术上的完整性。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张爱玲从“完整性”出发区分艺术和历史之间的差异,其认为历史可能就是“没有系统的”,如果要对它进行客观呈现,就不能像文人构思小说那样赋予“混沌”的现实一种“和谐联系”,当历史以和谐的联系呈现时,也逐渐迈向虚构性而非真实性。无疑,“一旦这种历史虚构形成,当它们成为一种主宰着政治秩序的故事或叙事时,我们其实离真正的历史越来越远”。“非思”就是要把握“混沌”的现状,重拾历史的碎片,以此替代甚至打破“完整性”与“系统的”的现实呈现,而这才能从虚构的想象之中回到底层民众的生活层与思维层。由此看来,“非思”是对两种典范性叙事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具体地讲,一是突破表象仅是真相的反映而非真相本身的理论,进而认定“纹理”和“褶皱”即真相;二是对用连贯且完整的逻辑叙事来整合历史的行为进行反思,重新将混沌或者碎片作为历史本原的呈现。
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曾讲道,历史完整性和系统性的叙事反映的是“当前社会体制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又反过来“解释了他们对于历史演进形式和历史知识必须采用的形式”。依据现实情境而言,底层民众并非“社会体制的价值”的制定者和主导者,他们仅仅被设定为社会体制价值的遵从者与服从者。因此,“非思”正是回到底层民众的话语世界,回到那些语言碎片当中,用断裂性方式实现对具有系统性与逻辑性的统制思想的突破,进而重塑新的思想体系。也就是说,“非思”不仅仅是对统制性思想的介入,还试图对它进行重塑。就重塑新的思想体系而言,其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不变更原有的框架,即在维持该框架的基础上置换主导者,以此建造新的思想体系;另一种则与此有别,它是跳脱原有的思想框架,以一种超越视角展开新的话语创造。与第一种方式相较,第二种远为激进,而“非思”的思想重塑方式,正是以后者的方式进行。在阐述第二种方式之前,有必要对第一种方式稍作说明。五四时期的中国曾高呼过一个口号,那就是“劳工神圣”。为了改善底层劳工的生活处境,不少激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找寻社会改造的办法,其中陈独秀就认为,劳工处境的改善离不开其自身的思想觉悟,思想的自主与解放,则是摆脱目前资产阶级和军阀势力剥削与压迫现状的重要条件。为此,陈独秀讲道,“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陈独秀有关“劳心者”与“劳力者”关系的重构或者再定位,看似打破既有的压迫性框架,但实际却仍旧是在原有的范畴之内进行调整,并未实现对既定的“统治—被统治”结构的突围。质言之,陈独秀尽管在为底层劳工谋求思想上的主导性,然而主导性的获得,并不是以彻底拒斥而是接受原有的象征体系来获得。
确然,根据朗西埃的言说旨意,第一种思想重塑方式看似经历了解构到重构的过程,但这种翻转并未创造新的价值体系,而“非思”的思想重塑,自然不同于此,它类似齐泽克言及的彻底改写坐标系的行动。在齐泽克看来,“‘行动’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打破现存的象征体系,行动不能在先存的象征秩序框架内运作,而是去改变决定事物的框架本身”,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框架的突破,则是当服务员问要“咖啡或茶?”时,回答者“并不是按照对方提出的框架作答,即在两个选项之中择一或者拒绝两者,而是诡异地回答:‘是的,请!’”。(林哲元:《空无与行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30页。)作答者已然突破既有的问题框架,从另一个维度或者新的框架进行回应,而这种回应实际上是对原有的问题框架的真正突破。在朗西埃看来,“非思”就是要寻回底层民众的“话语”、“声音”、“言谈”,这种找回虽然指向对既定的统制话语的否定,但是依然需要注意,如是否定并不延伸到另一个方向,即赋予“来自下层的思想”神圣性,也就是说,并不是从一个极端否定走向另一个极端肯定。“非思”对于来自下层声调的传达,恰恰是对日常的注视而非对神圣的塑造,是对表象的肯认而非对高悬头顶的指令的信仰,是将零言碎语视为自主呈现而非借严肃且逻辑的表述作为虚假掩饰。“非思”激活了底层民众的语言功用,并用它唤询了自己主体的身份,他们不是向上层行注目礼,也不是自我夸耀,而是在这套逻辑之外,建筑新的地基与营构新的话语空间。
如果“非思”是在统治阶层或知识精英的思想话语之外进行开拓,那么,来自底层民众的“非思”尽管被视为思想的对立面的出场,但这里的“对立面”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一种超越。“非思”既是思想的暗域,因为它被后者遮蔽;同时,“非思”着眼于思想的暗域,因为它要从后者中突围。在此,“非思”并不是对思想的悬置性考量,也不是延迟性颠覆,而是一种当下性的爆破。柄谷行人在《思想地震》中指出,当我们与世界对峙时,往往存在多种判断,其中包括认识判断、道德判断以及审美判断等,因此,科学家在采用认识判断观察事物时,会暂时悬置道德判断与审美判断,只有通过这种悬置,才能在理性的分析之下认识对象。然而,对于底层民众来说,他们采取认识判断的时候,往往也暗含着道德判断,换言之,他们一方面运用认知判断辨别社会统制性思想的真与伪,另一方面又将道德判断纳入进来,从善与恶的角度进行区分。这截然不同于医生给病人动手术,只从认知判断着手诊察病人病情,而悬置病人的道德状况。由是而论,针对底层民众的思与行,如果先行从逻辑性出发对其进行整合,往往会忽视他们内在的混沌性,混沌并非负面词汇,而是一种修辞,其意涵指向的是主体生产动能的复调回归。与此同时,“非思”在思想中突围,并不是将重塑思想的实践和主体实现的目标延迟到无限的未来。按照一般的突围法则——“应当学会等待,而不丧失耐心:如果我们行动得过快,这个行动就成为贸然行事”,也就是说,如要冲破既定的思想樊笼,首先需要沉淀,进而巩固力量,再次则是等待时机,最终才是付诸行动。但就实际情况而言,“从来不会有行动的所谓恰当时机”,即从来不会有所谓成熟的突围条件,因此,关键在于通过行动创造时机。“非思”的非延迟性颠覆,正是在思想逻辑强调理性缜密计划之外,肯定底层民众的自动性和自发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无不意味着,突围工作不是延迟,而是将任何一个时刻作为紧急时刻,把握时间维度的每一个“当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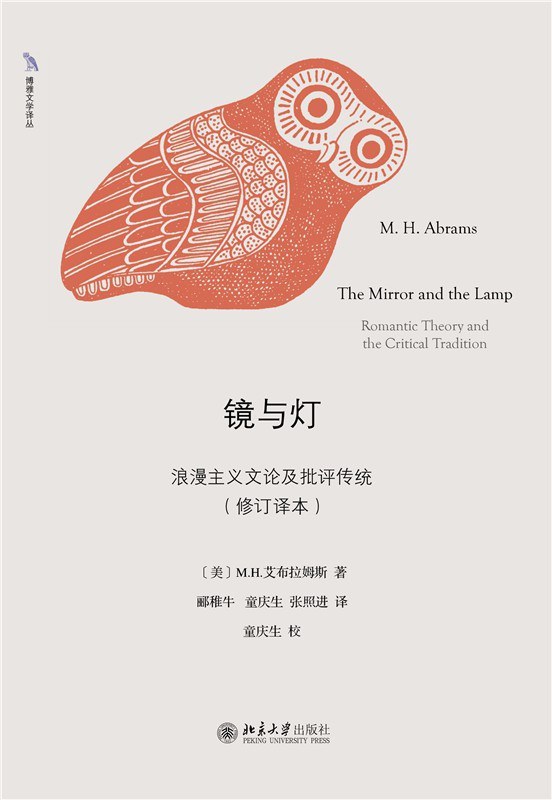
《镜与灯》书封
朗西埃讲道:“思想赋予非思一种特殊的力量。”这种力量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在与思想的对位过程中,“非思”同样获具自我照明的属性。美国批评家艾布拉姆斯在其著名小说理论著作《镜与灯》中,提出“镜”与“灯”这两个重要概念,其中“镜”强调的是“心灵感知者就是反映外在世界”,其对应的是“模仿”的书写传统;而“灯”凸显的是心灵的创造性,并视创造者本身即是“光之源泉”,其对应的是“表现”的书写传统。若借用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理论进行分析,思想尽管赋予“非思”特殊的力量,但是“非思”并不是思想的“模仿”,或者镜像的反映,而是“灯”的继承,它将自身作为一束光源,照亮自己的领地。当然,“非思”的自我照明属性,针对的是思想背后暗含的启蒙理性传统,而这套启蒙理性传统,既预设了上层与底层之间的位势差异,又给定了上层为下层指明出路的不可撼性,除此之外,更是赋予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进步性特征。正因如此,当“非思”发现自身同样内具照明属性,其对思想的突围与重塑,已然从支配与被支配、主导与依附的范畴转向从思想的历史连续性中爆破出来,进而建立新的坐标体系。这一点,正是突围实践的本质特征。本雅明就曾指出:“如果一个历史对象需从历史的连续体中爆破出来,那是因为其单子结构要求这样做,这个结构正是在被爆破出来的对象上的第一次清楚显现。”总括地讲,“非思”从思想构筑的历史连续性爆破出来,既是对原有的统治结构的批判,又是展开新的解放叙事的重要开端。
“非思”尽管内在于思想之中,但思想并不自动呈现“非思”,“非思”是经过历史的爆破而得以主体性角色显身。作为“非思”之域的底层民众世界,他们的声音、语言、想法并未因他者的传达而被听见、理会、可知,因为来自下层的声音可能含混不清,语言可能支零破碎,想法可能既混沌又杂糅,这些特征都将因思想的逻辑化与系统化整合,最终变得失真。因此,“非思”对于思想的突围和重塑,需要从历史的歧出之中找寻出口,无论是“纹路”还是“褶皱”,无论是“只言片语”,还是“插科打诨”,这些都是底层民众历史逻辑的真实呈现。按照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的说法,“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应视为历史的弃物”。历史动能和潜能,有时正藏匿在这些边角“弃物”之中,他们既是对完整性与逻辑性的思想叙事的打破,同时又是对历史本真的重新探寻。“非思”是历史的歧出,也是历史的实在,但决非历史不可抵达的暗域。因此,“非思”对于思想的突围和重塑,其最终目的不是消解思想,而是超越思想构筑的支配性或者统制性话语霸权,使那些来自下层的心声不仅可以言说,更且可以自主的方式继续言说。